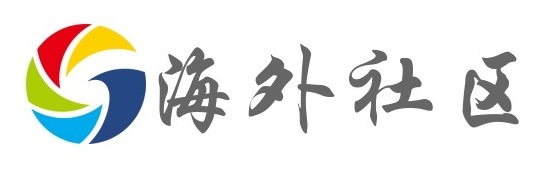失眠(不寐)的定义、分类及其中医学历史沿革
失眠,中医学又称之为不寐。“眠”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为:“眠,翕目也。”失眠,就是无法闭目入睡。《中医内科学》将不寐定义为:“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证,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、深度的不足。轻者入睡困难,或寐而不酣,时寐时醒,或醒后不能再寐,重则彻夜不寐。”常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、生活、学习和健康。西医失眠通常指患者对睡眠时间和(或)质量不满足并影响白天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。失眠可分为“入睡性失眠”“睡眠维持性失眠”和“早醒性失眠”,实际上一般失眠患者,常为混合性失眠,往往同时存在上述二至三种表现。
一、历史沿革
早在先秦两汉时期,中医学即对不寐病证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。不寐在《黄帝内经》中又被称为“不得卧”“不得眠”“目不瞑”。关于不寐的病因病机,《黄帝内经》以昼夜阴阳节律为出发点,以营卫运行为理论基础,确立了营卫阴阳为主要理论的睡眠学说。《灵枢·口问》云:“阳气尽,阴气盛,则目瞑;阴气尽而阳气盛,则寤矣。”《灵枢·邪客》云:“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,则卫气独卫其外,行于阳不得入于阴,行于阳则阳气盛,阳气盛则阳 满,不得入于阴,阴虚故目不瞑矣。”《灵枢·大惑论》云:“卫气不得入于阴,常留于阳,留于阳则阳气满,阳气满则阳 盛,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,故目不瞑矣。”提出了不寐的病因为卫气行于阳,不得入阴,这一理论,是中医学关于不寐证最早的认识,它被后世医家作为不寐病发生的总病机。再如《素问·逆调论》云:“阳明者胃脉也,胃者六腑之海,其气亦下行,阳明逆不得从其道,故不得卧也。《下经》曰:胃不和则卧不安。”表明脾胃不和,痰湿、食滞等邪气内扰可致不寐。《难经·四十六难》云:“老人卧而不寐,少壮寐而不寤者,何也?然,经言少壮者,血气盛,肌肉滑,气道通,荣卫之行不失于常,故昼日精,夜不寤也。老人血气衰,肌肉不滑,荣卫之道涩,故昼日不能精,夜不得寐也。故知老人不得寐也。”进一步提出了年龄因素可影响营卫运行,进而引起不寐。
汉唐时期,东汉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提到少阴病不寐,“少阴病,得之二三日以上,心中烦,不得卧”,少阴热化,心火亢盛,热邪扰心可致不寐。《金匮要略·水气病脉证并治》云:“心水者,其身重而少气,不得卧,烦而躁,其人阴肿。”《金匮要略·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》云:“支饮亦喘而不能卧,加短气,其脉平也。”均提出阳虚饮邪偏盛,上扰心神所致不寐,均为邪实表现。而《金匮要略》中“虚劳虚烦不得眠”的酸枣仁汤,《伤寒论》中“脉浮而大,浮为气实,大为血虚……干烦而不眠”,又进一步提出不仅邪实可致不寐,气血阴阳亏虚亦可致不寐,尤其重视心神在不寐病证中的重要作用。
隋唐宋时期,巢元方进一步提出不寐的脏腑病机分别为心热和胆冷,《诸病源候论》云:“冷热不调,饮食不节……故烦躁而不得安卧也。”火热温邪最易扰人心神,发为心烦不寐之证;大病久病后多虚,体质虚弱,体虚血少,无以濡养心神,神不守舍,发为不寐,如《诸病源候论》云“大病之后,脏腑尚虚,荣卫未和……故不得眠”。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“心脏脉论”中曰:“五脏者,魂魄之宅舍,精神之所依托也,魂魄飞扬者,其五脏空虚也。即邪神居之,神灵所使鬼而下之,脉短而微。其脏不足则魂魄不安。魂属于肝,魄属于肺。”可以看出,孙思邈以五脏藏神(心藏神、肝藏魂、肺藏魄、脾藏意、肾藏志)的生理功能为基础,认为脏虚邪居,魂魄不安,而发不寐。
金元时期,刘完素重视火热致病的广泛性,提出了“阳气怫郁”理论,如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云:“热甚于内,则神志躁动……不得眠也。”张从正重视情志致病因素,提出不眠与嗜卧皆由思气所致,认为思虑伤脾导致气血失调,以致卧而不得眠,如《儒门事亲》云:“一富家妇人,伤思虑过甚,二年不寐。”李杲重视脾胃虚损可致气血亏虚,心神失养而不寐。朱震亨论火证,以滋阴降火为主要治疗方法,多从郁、火、痰的角度来治疗不寐证。
明清时期,医家综合发展了传统病因病机理论,将阳不入阴、脏腑气血、精神情志等融会贯通,全面发展了不寐证的病因病机学说。如明代张介宾在《景岳全书》中将失眠分为虚实两端:“不寐证虽病有不一,然惟知邪正二字则尽之矣。盖寐本乎阴,神其主也,神安则寐,神不安则不寐。其所以不安者,一由邪气之扰,一由营气不足耳。有邪者多实证,无邪者多虚证。”《医宗必读》将失眠概括为“一曰气盛,一曰阴虚,一曰痰滞,一曰水停,一曰胃不和”五个方面。《张氏医通》提出痰涎不寐,“盖惊悸健忘失志心风不寐,皆是痰涎沃心,以致心气不足;若凉心太过,则心火愈微,痰涎愈盛,惟以理痰顺气为第一义,导痰汤加石菖蒲”。《医林改错》言血瘀不寐“夜睡梦多,是血瘀,此方一两付痊愈,外无良方”,“夜不能睡,用安神养血药治之不寐者,此方若神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