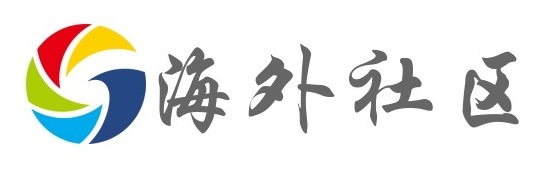张仲景对眩晕致病因素(痰饮)的论述
眩晕是目眩和头晕的总称。目眩以眼花或眼前发黑、视物模糊为特征,头晕以站立不稳或感觉自身或外界景物旋转为特征,二者常同时并见,故统称为“眩晕”。轻者闭目即止;重者如坐车船,旋转不定,不能站立,或伴有恶心、呕吐、汗出,甚或昏倒等症状。
一、历史沿革
眩晕是临床常见病证,最早见于《黄帝内经》,其中有“眩冒”“目旋以转”“眩”等多种称谓。唐代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始称“眩晕”。
历代文献中将眩晕称为“眩”者众多,虽其记载仅为“眩”而未提及“晕”,但从其病机及临床症状或治疗方法来分析,该处所言之“眩”,所包含的意义实际与眩晕之义相同。例如《灵枢·卫气》云“上虚则眩”;朱丹溪云“无痰则不作眩”。张景岳云“无虚不能作眩”,其在《质疑录》中论“无痰不作眩”时曰“眩者,头晕也,眼有黑花,如立舟车之上,而旋转者是也”。这一解释明确了“眩”代表眩晕之义,即把眩晕称作“眩”。
历代文献中有关眩晕的相关病名记述还有很多,如“风”“眩”“眩运”“虚眩”“风晕”“旋转”等许多不同的称谓,即便同一医家在同一文章中对眩晕范畴的描述都会出现多种,在描述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区别。历代医家还将晕分为“血晕”“气晕”“痰晕”“火晕”“湿晕”“暑晕”等,名称虽多,但其与眩晕范畴有关的命名无非包括了定义眩晕的两个方面的内容:一是眼黑或眼花视物模糊;二是感觉自身或外界景物运转不定,感觉部位定位在目与头。故后世医家多以眩晕命名,一直沿用至今。
《黄帝内经》认为眩晕属肝所主,与髓海不足、血虚、邪中等多种因素有关。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云“诸风掉眩,皆属于肝”,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云“木郁之发……甚则耳鸣眩转,目不识人,善暴僵仆”,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云“厥阴司天,客胜则耳鸣掉眩”,《灵枢·海论》云“髓海不足,则脑转耳鸣,胫酸眩冒”,《灵枢·卫气》云“上虚则眩”,《灵枢·大惑论》云“故邪中于项,因逢其身之虚……入于脑则脑转,脑转则引目系急,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”。
张仲景认为,痰饮是眩晕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,对各种原因导致的痰饮眩晕进行了详细论述。痰饮水湿停聚体内,一方面使气机运行受阻,阳不上承;另一方面痰湿本身也可上犯导致眩晕。
金元时期,对眩晕的概念、病因病机、治法、方药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刘完素主张眩晕的病机应从风火立论,其在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中言“所谓风气甚,而头目眩运者,由风木旺,必是金衰不能制木,而木复生火,风火皆属阳,多为兼化,阳主乎动,两动相搏,则为之旋转”。而朱丹溪提出了痰水致眩学说,其在《丹溪心法》中强调“无痰则不作眩”“痰由火引动”。李东垣认为眩晕与脾胃关系密切,其言“夫饮食失节,寒温不适,脾胃乃伤……脾胃一伤,五乱互作,其始病遍身壮热,头痛目眩,肢体沉重”。李东垣认为眩晕多为脾胃受伤后,不能行其运化升清的功能,清不守上,浊不守下,清浊互干所致。
明清时期对于眩晕的发病又有了新的认识。张景岳指出“无虚不作眩”,其在《景岳全书·眩运》中指出:“眩运一证,虚者居其八九,而兼火兼痰者,不过十中一二耳。”张景岳认为其虚或因“上气不足”或因“髓海不足”,而妄行作劳、忧思恼怒、饮食失节、脾胃受病等是导致眩晕的主要致病因素。《医学正传》云:“大抵人肥白而作眩者,治宜清痰降火为先,而兼补气之药;人黑瘦而作眩者,治宜滋阴降火为要,而带抑肝之剂。”此外《医学正传》还记载了“眩运者,中风之渐也”,认识到眩晕与中风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。